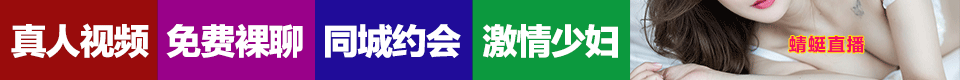我和老婆新婚不久,老婆大学毕业后当了个中学教员,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公司当业务主管,但是我们和岳母的关系不是很好。她家是城郊农民,有两栋楼可以收房租,还种了些菜来卖,家里人都在村办企业里上班,还有红利分,所以收入不错。我们家是城市居民家庭,前几年因为做点生意亏了钱,积蓄不多。因此,世道变了。农民开始嫌弃起市民来了。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。很多村子里的农民由于城市征地补偿,也分了不少钱。有一些家庭更不让小孩出外读大学(户口要转出去,没钱分),农民都娶农民,农民都嫁农民,本村的搞不定,就搞远点的,反正要农民。很多的本地农家的女孩子都嫁不出了。(高不成,底不就)到了最后,本来素质就不高,生出来的小孩的就更差了。很多年轻人都无所事事,吃喝嫖赌毒荡,无所不为。所以,我们的婚姻遭到很大的波折是正常的一件事情。
但出呼他们意料外,我的太太非我不嫁,历经各种困难还是和我在一起。(这些过程容后再述)婚后,我们买了套房子,她教书来,我上班,小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。由于,我们住得比较近,有时也回去看看他们。可每次都扫兴而回,每次都冷嘲热讽,令我们都不开心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解决这个问题,搞好一下关系。我们作了很多努力:过节给钱,买东西回去啊,吃饭都争着买单,回去多一点。慢慢地,她家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有一天,我们再回去的时候,岳母又旧病复发了,当着我的面奚落我太太。我老婆很不高兴和她发生了口角。但我却很冷静,为了家我知道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我的岳母,我发现这个女人毅力真强,挺可爱的,挺搞笑的。虽然她骂人的话不堪入耳。我心里暗暗发笑,会不会失调了呢?其实,以前我很讨厌她的,今天真的很奇怪?我反而有点同情,可怜她了。
前文书接上一回上回说到,岳母在奚落我们。我没发脾气,反而有点可怜她,看来我们还是关心得不够,是我们作后辈照顾得不周到。好,我们把画面定格下来。先说岳母的情况,她今年48岁,正值如狮之年。但不幸的是,我的泰山在一次“猎艳行动”当中,由于不注意,没穿雨衣,中了弹,引发了旧患,可能引至不能人道。(唉,真惨,奉劝各位” 猎艳” 时一定要穿避弹衣,不然祸害无穷啊!)想到这里,我望了望这个可怜的女人:她中等身材,留了一个短发蓬松,眼角有点鱼尾纹,牙齿挺白,有点哨牙是个标准农妇模样。整个身材干净利落,臀部,胸部,手臂,大腿看来都很结实结实,古铜色皮肤,一双大脚都起了老茧,可以参加轻量级的健美比赛了。(建议一些美眉要健美,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些田地种种)。她也有难处,找我们出出气也应该的。我对她以前那些种种不是也烟消云散了。我这个晚辈怎样帮她呢?我问我的太太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,她也去找了好多医生问了。也没有什么办法。
有一天,我的好朋友兼客户大头成找我吃饭。他是农村来我们这里打工的,开始学修车,几年后也打开一片天空,开了几个店舖。因为他的朋友都是一些五大三粗的人,我这样的很少,他觉得我很好,一直都很谈得来,婚前我们哥两都曾一起风花雪月,他有多少个女友我都知道,后来我们都成家了,他也有了小孩,过去我们的快乐时光也不再了。席间“兄弟,最近有何烦心的事啊,看你这样子”他拍着我的肩说。“说了你也帮不了,说来干嘛!”“你不说我咋知道,咋帮你”他用沙煲大的拳头捶了我一下。我把事情告诉了他。大头成是个爽快人“你的事就是我兄弟的事,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干杯。”我们如此这般地计划了一下“就这样定了”帮助岳母,表表孝心的机会来了。岳母打电话给我,叫我开车带她去买些治泰山” 富贵病” 的药,她也急啊,毕竟很久没搞了。我一口就答应了,接着我叫大头成准备一下。 这天,她穿得梢好点了,梳了梳头,有一种廉价香皂的味道。她穿了件花衬衣,一条黑裤子。可能有点不合身,不知道多少年前的。把胸脯绷得紧紧的,隐隐约约看见她的奶子挺饱满的。裤子也有点紧,内裤的裤头也露出来了,内裤下面的边也透过外裤让人看见了。看来找天和老婆去买件衣服给她了,免得她自己不舍得买。由于经常劳动,她少了通常中年人的那种臃肿,多了些矫健。看得我也不好意思。她很少出城,而城市变化也很大,所以她也不认得路了。我带着,她也感觉得挺开心的。我们买齐了东西,这时我的手机响了,阿成打电话来了。我告岳母说,“我有点急事要办,多了人去不方便的,您先去阿成档口坐坐,我去去就来。”因为,岳母也见过阿成的,所以也就同意了。大头成的铺面后面其实是个修车的工场,里面有三个学徒工,十来二十岁的样子,小明,华仔,阿友,个个身强力壮,一个师傅三十来岁是个一米八的壮汉叫阿锋,因为挺热的,都光着上身干活,满身黑汗。他们也很久没回过老家了,女人什么味道都忘了。有个女人进来,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。都现得特慇勤,搬椅的搬椅,倒水的倒水,递烟的递烟。虽然,我的岳母是过来人了,但这么多男人围着她还是第一次了,也看得满头大汗,拿出她的手帕擦汗。大头成穿了件T恤,倒也干净,可满面胡茬,满脸堆笑“阿姨好,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。”“经过这里,我有点急事,我出去一下。你们照顾一下我岳母。”我说。他们都跟我很熟。也知道今天要干嘛,纷纷说:“作哥你忙吧,我们会招呼阿姨的。”阿成笑着递了杯水给岳母(有墨西哥苍蝇的),“喝水,阿姨。”“谢谢,你们真乖”岳母接过水,擦拭了一下额头,喝了一口,口挺干的,见到这么多壮汉。我先把车开到隔壁,偷偷摸摸走了回来,原来工场的门不知谁关了,只留华仔看铺。我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向里看。阿成拉了一张破沙发过来,自己坐在上面,“阿姨,坐这吧,这舒服点。阿友把这张椅子搬走,不要看了你们,赶紧干活吧!是不是想扣工资啊”大头成装模作样地说。“唉,这么凶嘛。”岳母拿着喝了一半的杯子一边说一边坐了过去。“这帮人很懒的,不骂不行的。”阿成像个大哥的样子“慢慢教嘛,都是小孩子”岳母温柔地说,接着又喝了一口水。哇!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的。哦,原来她有骚的另一面,看来药力开始发生作用了
阿成真够朋友,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来帮我,今天的生意也不做了。得人因果千年记,事成之后,我要好好的报答他。我可怜的岳母这次有救了,我一定会治好她的。岳母觉得有点热了,把领口扣子脱了一个,把水全部喝完了。“阿姨,你热吗,我拿个扇子给你扇一扇吧。”阿成说。“不用了,我自己来。”岳母拿过扇,可是越扇越热,两个腿收紧了摩擦著。她也好像忘了旁边还有人了,又解开了一个扣子,露出白白的胸脯。“阿姨,你不舒服吗?”阿成的手放到岳母的大腿上,关切地问。“不知道,很热啊。有点头痛。”她闭上眼睛,喘着气说。“阿友过来,帮阿姨揉一揉太阳穴。”立刻那几个男人都跑了过来。阿友帮她按著头问,“好点了吗,我帮你按按肩吧”小明的手也过来了,抓住了她的手。“阿姨,我帮你按手吧”大块头阿锋也过来。“我按摩一下腰吧,好吗!”岳母有点迷糊了,嘴里应到“呣呣”,腿扭来扭去。我在门外看得,也兴奋起来。扭头一看,只剩我一个了。原来华仔打开后门,悄悄得跑了进去,抱着另一条大腿。不过,这也难怪,他们很久没碰过女人了。华仔和阿友的手慢慢得插进衣服摸到她大奶,阿成也偷偷地解岳母的裤带,小明也手没闲著也已经伸到裤头里去了,阿锋把自己的裤子也已脱了下来。看来,事情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。“你们在干嘛,放开我,我有老公的。”“我们是在帮你啊,肯定会令你很爽的。”阿成按着她一条腿色迷迷地说。阿锋铁钳般的手抓住她两只手,抬高到头顶。阿明继续解裤带并没有停下来。阿友已经把扣子全部解开了,露出岳母肉色的胸罩,她的大奶呼之欲出。看不出来,我的岳母里面还是挺白的,我老婆说得没错,由于里面晒不到的原因吧。“不要,不要。我年纪可以当你们妈了。”岳母由于多年的劳动比较强壮,非常有力地但徒劳地不停地作最后的挣扎。天啊!小明居然隔着内裤在舔她的私处,小明将岳母的裤子都脱了下来,露出一条粉红色的裤衩,阴毛露出几条在外面。他把岳母整个私处含在嘴里,隔着内裤的摩擦著阴蒂阜,从阴阜传来的刺激更强了。“啊……”岳母不由自主的一声呻吟,默许了。“贱货”大块头阿锋等不及解开的胸罩,从一旁拉下,岳母的左乳从胸罩中弹出,她的乳头可真大,有点发黑,毕竟年近半百了。乳房挺大的,有点下垂,晃荡著。阿锋一口便含住岳母的乳头,又吸又咬,乳头已经硬起来,而阿友另一手则握住岳母的右乳,很有技巧的搓揉,温柔的触感使她全身都发热起来。“不行…我女婿回来了…呜……”正想挣扎抗议时华仔一口便吻下来,华仔的舌头强伸进岳母的嘴巴,她咬紧牙齿不让得逞,但华仔丝毫不放松,强行突破关卡,他们的舌头接触便交缠在一起,这时我知道事情成功了。小明脱下她的鞋,用牙齿轻咬我的每一个带着老茧的脚指,我看见岳母打了个冷战,看来她有感觉了,我很开心。她的小腿上有些细细的绒毛,小明一根根地拔,岳母动弹不得。阿成慢慢的将岳母的大裤衩褪下,小明则接着把内裤从她脚上脱掉,这时岳母已经是全裸了,她的屁股不是很大,但挺结实的,小明“啪啪”地用手扇她的屁股,那两片肉都红了。她“啊……啊”的叫。她不再挣扎了,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。阿友已经将岳母的胸罩解开,在阿锋和华仔两人四只手帮助下,半穿在身上的衣服完全离开她的身体,这时,五个人将她翻过来,岳母像母狗一样,四肢跪在沙发上,而阿成则钻到她下面面向着她,小明半跪着,内裤正好对着她的脸。我看着他的手将他的阴茎掏出来,好大一支阴茎,比我的还大一点,小明将阴茎塞往岳母的嘴巴,我觉得她结婚这么多年,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事,但是出乎意料的是,她居然自动的吸吮起来。她的表现刺激的我全身更热了,真想冲进去。阿友抱着岳母,一只手抠她的肚脐眼,一只手使劲拉着她黑黑的奶头。口里的舌头也舔她的耳朵眼,搞得都是口水。接着,华仔一支热呼呼的阴茎抵住她的阴唇。阿锋的一只手轻揉着岳母的阴部周围,它已经泛滥了,粗大的阴茎轻轻的进入她的体内,华仔慢慢的在她体内抽送起来,跪着被干的快感令她呻吟,但是嘴里含着小林的阴茎,发出声音“……呣……呣……”“我来搞一下阿姨的屁眼,好吗?”阿成用手指按摩著岳母的屁眼。我敢打赌这是连岳父都没有摸过的地方“不要,不要啊……”岳母发抖的声音响彻车间。阿成把湿润的液体沾满她的屁眼,接着一颗较小的热弹压住屁眼,阿成居然要干岳母的屁眼。肛交这个名词自己从来不敢去想像,看来我有机会也要搞一搞。屁眼被撕开的痛楚和阴唇被摩擦的快感,令岳母大声呻吟“啊……啊”阿锋和阿友抓起岳母粗糙的手握住他们的阴茎,岳母用力的握住这两只阴茎,她用劲的上下搓揉阿锋的阴茎,阿友一边还蹂躏她的乳房,她越用力搓阿友的阴茎,阿友越用力揉弄岳母的胸部。阿锋用力地揪岳母的腋毛,一把一把的。而华仔一方面插著岳母的阴阜,一方面还吸允着她另一个乳房,全身上下无数的刺激让她快要疯狂。他们把岳母的肚皮咬得一道一道的。华仔和阿成的阴茎在这个发浪的中年女人体内相互摩擦著,估计她屁眼的疼痛早已消失,是一阵松弛和紧绷交织的快感,和阿友巨大的阴茎呼应着,她已经快要崩溃边沿了。他们把岳母的大奶掐来捏去,拍来晃去,像打着两个肉球,两个奶头也由黑变红。不停地问“阿姨,爽吗!满意吗”小明从她的大嘴中拉出他的阴茎,剩下的精液一股股的喷到脸上,岳母贪婪的用舌头舔著犹在的龟头,舔的龟头慢慢的变小,而同时阿锋和阿友也将他们的精液喷在岳母的乳房和臀上,喷到乳房上的精液顺着乳房由她的乳头慢慢滴下。 华仔几乎是和阿成一同射出,我看见她体内黄色的液体好像跟着阿成的阴茎抽出跟着泄出来,她全身软瘫在破沙发上。我隔着门缝看,肉棒涨疼,阿成他们真够朋友帮我一个大忙。其实,我很想进去,但还是忍住了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过了好一会儿之后,我感觉他们五个人慢慢的起身,温柔的用纸巾帮岳母擦拭身。“阿姨,爽吗。”阿成捏着她的奶头说。“肯定爽啦,这么多人服务她。”阿锋使劲拍著岳母臀部说。她羞怯地挣扎着爬起来,极度快感仍然留存在身上,五人的手恋恋不舍地摸着她奶子,阴部。温柔的抚摸让岳母得到很大的满足,挣扎好久之后才能够爬起来,戴上瘪了的胸罩,穿上皱吧吧的裤子,整理衣服。“阿成,我们要走了,谢谢你们照顾我岳母。”我若无其事地推门进去。“他们对我很好——”岳母被我吓坏了匆忙应到。“不用客气了,我们是好朋友,阿姨有空再来坐坐。”阿成说。“拜拜”那几个小伙子很不舍的告别。岳母疲惫不堪地挥了挥手。在回来的车上,岳母睡着了。我看了看她,嘴角还残留着一些痕迹,我拿纸巾帮她擦了擦,岳母一点反应也没有,真是太累了。她的脸色还有一丝红晕,可能还在刚才那些激动的场面里。我趁这机会,一手开车,一手悄悄地伸进她的衣服里,慢慢地在她奶头上打着圈子,在那下垂的奶子揉捏著。我相信岳母会对我们两夫妇好点了。果然,岳母对我们好像换了个人似的,平时比以前好了很多。而且,经常要求我带她去买药,当然除了阿成外,我还有很多朋友。例如,建筑工地的民工和工头,货运场的老板和他的搬运工们等等。岳母的心情非常好,脸色也好了红润很多,就好像吃了“太态口服液”看来性这个好东西比什么样药都要好。
【完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