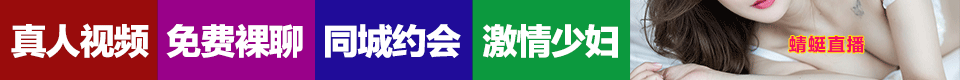我今年20岁,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,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。母亲是一个普通但美貌的家庭主妇,父亲是一个普通但英俊的公司高管,我本来惬意地享受着这普通的生活,直到有一天,一个男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
一天夜裏,我和朋友吃完饭回到家,看到了房门虚掩着,想到父亲在出差,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,我担心起来,从门缝偷偷看进去,居然看到了母亲赤裸上身,被绑在了一张椅子上,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入室抢劫,可家裏明显已经被翻过了,他爲什麽还不走呢?我们家住的是别墅,邻居住得都不近,我暂时只能打电话求助。可看到母亲浑圆坚挺的胸部,我不知爲何停下了。
绑匪开始恐吓母亲,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父亲公司竞争者派来的,目的是窃取父亲的商业机密。他见母亲并没有屈服,就扒下了母亲的裙子和内裤,要侵犯母亲。可不知爲何,本该惊恐的母亲却像看到这一切的我一样,显得有点兴奋。
绑匪被母亲激怒了,开始侵犯母亲。就在我感到不安时,母亲却主动配合了起来,扭动腰肢,好像在渴求着。就这样,绑匪解开了母亲,两人缠绵起来,几十分锺后,母亲已经骑在绑匪身上,获得了主导。又几十分锺后,绑匪败下阵来。我惊讶地目睹了这一切,全身欲火翻腾。
母亲最终放走了绑匪,并放言。她知道伤害别人性命对他们也不好,如果想得到父亲的东西,就操赢了她。我躲在屋外的灌木丛,没有被绑匪看到。之后,我过了一小时才回家。一是爲了平静心情,二是爲了给母亲时间打扫。
从那天我才知道,我的母亲是个蕩妇,所以我也是天生的淫女。就是如此,我没有把母亲的秘密告诉父亲,也没有让母亲知道我看见了那天的大战。比起这些,我更希望看到更多母亲淫蕩的样子。
我给家裏安装了摄像头,爲了记录之后可能发生的豔景。不知道是不是被母亲诱惑了,老爸的竞争者居然真的拍了一批批的壮汉和母亲交手。可是,母亲居然一次都没有落下风。两个人,三个人,四个人。内入,口交,肛交,捆绑,震动棒,电击器。所有我见过没见过的调教方法都用在了母亲身上,但是最终,母亲总是能用她那饑渴的淫穴榨干对方,大获全胜。一次次的交手,让我不仅对母亲産生强烈的性欲,还对母亲越发敬重。没想到一个天生的蕩妇居然可以保卫这个家。
就这样过了一年,竞争者来了十几次,都没有打败母亲。而这次,他们又来了,走在三四个壮汉前,领头的,却是一个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。这就是老爸竞争者公司的老总,没想到是这麽有气质的女人。而这次,她就是母亲的对手。
她和母亲都脱光了,在床上互相拥抱着接吻。我一开始就确信了这女人只是想用母亲发洩欲望,因爲毕竟这麽多根巨龙都没有制服母亲。可接吻几分锺后,母亲居然开始抗拒,想推开女老总,但是被女老总按住了头,继续强吻着。在之后,母亲慢慢被占据了主导。母亲眼神变得迷离,身体开始扭动,在女老总放开母亲时,母亲居然像刚刚做完爱一样娇喘着,口中挂着晶莹的涎丝。没想到这女老总的吻技这麽高超。
紧接着,没有给母亲丝毫喘息的机会,女老总把母亲转过去抱在怀裏,擡起母亲的双腿压在自己的双臂下,这样母亲的屁股和下体就翘起来了,这样羞耻的姿势,母亲明显感到不安,我第一次看到母亲面带慌乱的挣扎。可女老总的手指已经摸到母亲的阴唇上,轻轻揉着,另一只手在母亲的黑丝脚底上慢慢抚摸、挠痒。母亲一开始在忍耐,但是很快地,母亲娇喘起来。我知道母亲占了下风,这样下去不妙,没想到女老总的实力居然在母亲之上。可这时,我并没有选择帮助母亲,比起母亲的安危,我期待的居然是下面的内容。
母亲被女老总摸着阴唇,几分锺后,女老总掀开了保护母亲下体的唯一一层蕾丝内裤,然后把手指插了进去。母亲不愧是天生蕩妇,她一开始居然忍住了呻吟,可这只是一瞬,女老总快速抽插时,母亲马上浪叫起来。我第一次听到,这简直是淫蕩的交响乐,母亲的声音都像性药一样有催情的功效。很快,母亲居然被玩弄到失神,最终,随着高潮的浪叫,母亲潮吹了,像射精一样喷出了淫液。母亲彻底输了。此时等在一边的壮汉也把防御被破的母亲围了起来,準备好彻底摧毁她,母亲第一次绝望地求饶着。可是,这只是地狱的开始。母亲被几人像性玩具一样狠狠操起来,原本保卫这个家的无尽阴道已经被女老总攻克,现在已经敏感得不行,在壮汉的狂轰滥炸下一次次潮吹,无敌的阴道彻底被废掉,变成了只会贪婪吸收快感,侵蚀母亲神智的性具。
几人足足干了我母亲一个小时,母亲已经满身精液,失神着昏迷过去。他们却没有寻找父亲的机密,而是带走了母亲。
从那之后母亲失蹤了,父亲很担心,但是我却告诉她母亲去朋友家裏了,不需要联系她。因爲我知道,她会回来。
果然,有一天,母亲回来了,她迫不及待地就要和父亲做爱,父亲明显被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欣然接受了。母亲把父亲脱光,却提出要玩新花样。她把父亲的手脚拷在了床上,之后却走了出去,她回来时,赤身裸体的女老总也跟了进来。父亲非常震惊,可我明白,母亲已经被彻底调教成了女老总的性奴。
从他们的对话我知道,原来女老总曾经尝试过把父亲囚禁起来调教。可父亲和母亲不同,他并不好色,阴茎的耐力也超强,女老总甚至完全没有让他射精。父亲在逃脱后当然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,因爲证据不足也无法对女老总怎麽样。没想到的是,女老总居然对母亲下手,把母亲调教成搾精性具来榨取父亲。父亲已经对母亲的身体熟悉,在母亲的口交下,巨根很快勃起。母亲像十足的蕩妇,慢慢蹲下,用原本保卫这个家的阴道吞下了父亲坚不可摧的巨根,然后一次次吞吐,一次次摧毁它的防御。女老总则用她的指技玩弄父亲的菊穴。在两个绝世蕩妇的摧残下,父亲不可能被强制射精的阴茎变得越来越脆弱,父亲大汗淋漓,可依然无法抵挡双重快感,很快,父亲呻吟着请求母亲停下。可母亲现在是只想着性交和快感的母狗,把自己的丈夫调教成竞争者的性奴,这种羞耻可以带给她极限的快感。就这样,母亲加快了频率,父亲的坚挺巨根被击败了,在父亲的怒吼下射出了浓浓的精液。母亲和父亲一起高潮,可母亲却没有停下,依然套弄着,父亲痛苦地哀嚎,可马上又呻吟起来,随着又一次高潮,父亲再次喷射,母亲这次把父亲的巨根从身体裏拔了出来,父亲喷射的精液差点喷到房顶。母亲继续用手大力套弄父亲的肉棒和龟头,父亲彻底崩溃了,拼命挣扎。可随着一阵抽搐,父亲的精液再次被榨出,喷出的精液落到父亲的脸上和嘴裏。然而这只是地狱的开始。母亲居然含住父亲的肉棒再次搾精,父亲这次失神了,只有呻吟。又一次射精,父亲不知道积攒了多少欲望,又一道精液沖到父亲身上。又一次足交,又一次口交,父亲已经浪叫起来。曾经被女老总费尽心思也无法射精的肉棒现在一次次喷洒精液。原本是父亲守护神的坚不可摧的巨根变成了快感的生産器,帮助母亲和女老总摧残和父亲的理智。最终,父亲的肉棒垂了下去,再也立不起来了。父亲全身精液,惨败在自己妻子手中。
父亲也被带走了,但是父亲和母亲不同,他的性格比较刚强,想把他调教成性奴是很难的。但是,女老总也不会让他好过,现在的父亲被机器分开双腿拘束,双手被拘束在身体后面,粗大的肉棒被一个管状搾精器吸住,口中连着一根软管输送营养液,性药和催精药,让父亲可以无限産精。而在母亲没日没夜的调教下,父亲坚不可摧的肉棒已经废了,现在即使是轻微的抚摸都可以让它爆发式喷精。曾经耐力远超常人的父亲现在居然变成了可以无限喷精的淫蕩精奴。父亲的精液现在甚至可以被卖出,父亲自己也可以作爲展品展出,他现在有了新的名字,射精机器。他现在甚至连做人类的资格都没有了。而我,很喜欢他的新名字,因爲只有他变得更淫蕩,才符合这个家族。现在我和我的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父亲最激烈的搾精作业,尽快把他调教成像我们一样的性奴。
我生活在一个淫蕩的家族,我的母亲是淫蕩且妖豔的搾精性具,我的父亲是色情且性感的射精机器。而我是一个下流且放浪的精液性奴。